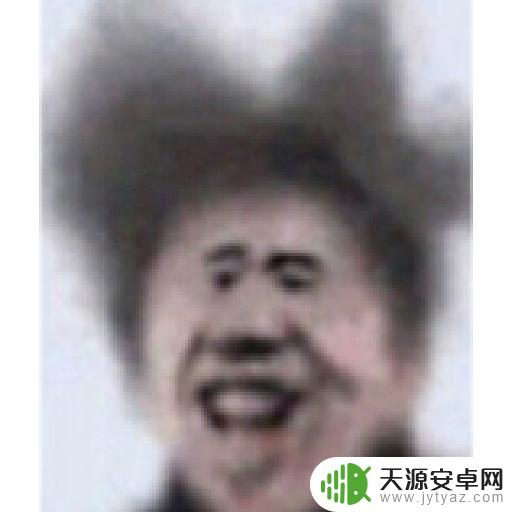你以为翻开一本历史书,一切就是那些君王、帝国、名将。可谁又能说,真正左右这些巨轮转向的。不是一群躲在黑夜里的人——他们随时可能被误解,被追捕,哪怕最终并没有留下名字。所以,历史表面的光鲜下面,总是埋着斗争,甚至血——它悄声无息,却无处不在。
行在暗夜,侍奉光明。万物虚无,但偏偏人心不甘。

如果你问“刺客信条”系列为什么被那么多人念叨,说起来还带着点痴迷。有人会告诉你:这是穿越千年的人类秘史,是游戏,但比游戏大得多——它把我们习惯的小人物、巨大阴谋、背后的推手、信念的选择,都拉到了一场看不见终点的大戏里。你不能说它百分之百是真的,但你如果真有点认真研究历史,还真不好说多少“虚构”横跨了“现实”的边界。这里的每个人,都是命运深夜里那一束光,也是一把被握得紧紧的刀。
不过,咱讲故事,还是得从最早的头说起来。如果这个世界里真有一群“先行者”——伊述人,那就意味着我们全人类其实是别人手上造出来的作品。听着有点荒唐,可偏偏又像极了现实中那些我们无法掌控的环节——比如天灾,比如基因,比如生死。伊述人,那帮玩儿起DNA、造神神器的家伙,留下一堆瑰宝和陷阱。问题是,神器自己管不了自己,最终哪怕是最聪明的种族,都会败在自己手里。内战爆发、王权更迭、偏偏一场大灾难,什么都得还回去。

而到了某个点,这场“造人”的游戏马上不受控了。夏娃和亚当挺身而出,哪怕一无所有,也不肯乖乖受锁链。于是“人类自由意志”这事,第一次真正在混沌中点亮。一把伊甸苹果,换来的是血与叛乱,是一场“被造物者反抗造物主”的十年战争。说到底,“刺客”这俩字背后,就是一声:我想靠自己选择。
但偏偏天不遂人愿。灾难不是靠勇气就能扛过去的。伊述人合计了不少自救方案,什么超级计算机、硬核科技、极光装置,都未能挽救自己。所有的“救世”努力,真正做成的是——让自己灭绝,把舞台让给人类。那些没来得及走完的方案,像世界树中的上传灵魂,最后只留下七零八碎的意识在时间里默默游荡。你说这玩意儿像不像我们偶尔深夜做梦,好像全世界的历史,都只是前人的回音。

可就算如此,也有不肯甘心落幕的家伙,比如朱诺。这个名号,一听就是狠人她妈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种族消亡,却在最后一刻偷偷动手脚。把自己藏进大殿、绑在被救方案里,就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再次执掌生杀。说到底,天才与疯子只差一口气,对于权力的执念,不分古今,谁也跳不出这个“轮回”。
伊述灭绝后,留下的“混血儿”成为新一轮游戏的主角。他们继承了那一点点“超能力”,也带着上一辈子的残酷回忆。鹰眼、异能,这些常看见的技能,其实不过是基因里的残影。而血统这件事,从来不是谁能说了算的。偶尔有人生而不同,可那一条独行难返的路,注定是“异类”的宿命。

镜头一转,我们都还记得亚当、夏娃的儿子——该隐。兄弟阋墙,这听着就让人叹气;可谁知道某天,这样的“原罪”竟成了圣殿骑士们一直挂在身上的“印记”。他们认定:人类必须接受铁的秩序。这种想法,只要心里有点自尊的,都会反感;但放在年代久远的历史上,猜不准是谁更“对”一些。
圣殿与刺客的纠葛,真要细说,哪朝哪代都有。上古的、近代的、东方西方,都绕不开这个轮回。列奥尼达斯的矛、大流士的袖剑,每一把兵器后头都是一茬人的血和愤怒。刺客坚持自由,圣殿信奉秩序。几千年了,没哪个大人物能真的灭了对方;世界上也一直没少过新的参与者。

你随口一提哪个历史人物,背后多少都是一场戏。比如卡珊德拉,明明只是想找家人,顺带在希腊神话的废墟里翻了半辈子,也没能彻底问清“谁是自己”。她和大流士、奈塔卡斯的纠葛,是爱情、是传承、更是一种不得不承认的责任。艾匹底欧斯会不会责怪母亲把自己“扔”去异国?谁也不知道。很难想象,那批穿着皮甲、抓着武器的人,夜里睡不着的时候,会不会也想起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那个水果味道。
当然,有些选择,根本不由人做主。魏羽手里的断矛,最后走进了另一个年代。从秦始皇的阴影到安禄山的乱世,这一截武器卷进一出又一出的权谋与复仇。历史很多时候就是这样:一根“矛头”,流浪千年,不管谁持有,都没法彻底安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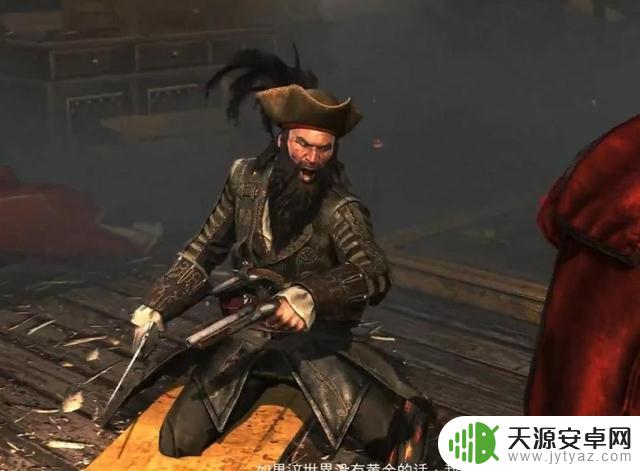
而刺客和圣殿骑士的故事延绵不绝,换了一茬又一茬身份。曾经在罗马混迹的贵族,后来成了逃亡的刺客;埃及艳后和凯撒的纠葛,背后藏着更大的组织角力。阿泰尔、艾吉奥、艾沃尔……每一位,年轻时都要经历至亲离散、背叛加身。成年以后的路,哪怕披着披风、带着神秘,也要面临失误、惩罚、复仇、成长。
就像艾吉奥,十七岁那年一夜成了家破人亡的无主少年。扑面来的不是仇人的利刃,而是“谁还可以信”的天问。他加入兄弟会,一边找答案,一边在血泪中成长。后来半生都在追寻“灯火”的那头,却也没真正过上安稳日子。迷雾弥漫的佛罗伦萨、群星稀疏的马西亚夫,成了他安放迷惘的地方。

当然,这场抗争并不只是男人的游戏。中国的明朝,少芸不得不远走他乡,逃亡、复仇、潮起潮落。她去意大利寻求帮助,带回的不是希望,而是下一轮血雨腥风。她不会知道,她短暂的平安,就是别人口中的另一个故事的起点。
文明换了几轮,矛盾依旧没变。和你隔夜喝茶的朋友,昨夜还在讨论秩序到底需不需要代价。英伦的工业城市,还是漂泊在加勒比海上的私掠船长,那种“生不由己”的感觉谁都懂。海瑟姆、谢伊、康纳、亚诺……他们拼杀半生,到头来却只能在庞大的世界机器前头,被碾过或者重生。

闲言碎语,这戏讲到近现代,也是一样。大公司变成新一轮黑暗之手,“基因记忆”这种说法,听起来像玄学,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都有点遗传的桀骜。阿布斯泰戈研究数据,戴斯蒙德、蕾拉、无数“样本”卷进机器,仿佛整个时代的人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玩弄。有点像我们上班用社交软件,信息都不再属于自己。历史,就是这样冷冷地照进生活。
故事说到这儿,有些人消失了,有些人还在等出场。即便神秘的圣物、极光仪、世界树这些词听着遥远,咱们日常琐事,也常常在重复同一组难题:是遵从本心,还是顺应权威?是“做人如刀俎”,还是哪怕偷偷地当一回渺小的鱼呢?

留下的悬念还很多。有的路像断剑,有的选择像染血的披风,总有人怀着各自的信仰,行走在混沌与光明的缝隙里。你问他们,这样一生是值还是不值?
可能没人能说清。可人虚无里,“侍奉光明”,这一句还挂在心头。兴许哪天,黑暗里那点微光,就是你我的答案。

——讲到这里,也许你才发现,这戏还没完呢。